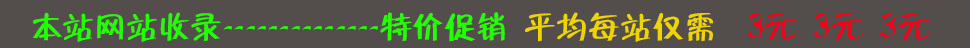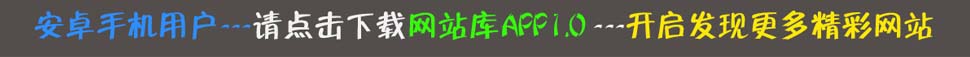2021社區之殤:靈氣的阿北和喪氣的豆瓣
來源:本站原創 瀏覽:793次 時間:2022-01-01
命運的鐘聲,正向著中文互聯網社區,敲出振聾發聵的警告。
前一段,處于臺風中心的是豆瓣。
12 月 1 日,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人約談豆瓣網主要負責人、總編輯。
對此,豆瓣發布公告稱從 2021 年 12 月 2 日 0 時- 2021 年 12 月 17 日 0 時期間,暫停“小組”回復功能的使用,并暫停小組“精選”頻道的內容更新。
更多的“敲打”,接踵而來。
12 月 9 日,豆瓣App因違規收集用戶信息,被工信部下架; 12 月 13 日,央視點名豆瓣存在水軍刷分控評現象。
圖片
全網的注意力、自媒體的輿論,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聚焦在豆瓣之上了。只是這一次,不再是像數十年前的追捧與高歌,而是充滿了疑惑和質問。
但豆瓣,并非唯一受到監管注意的對象。
小紅書啟動新一輪“虛假營銷”專項治理,首批 29 個涉嫌虛假營銷的品牌被封禁;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,新浪微博被實施 44 次處置處罰,共累計罰款 1430 萬元; 12 月 20 日,北京網信辦依法約談處罰知乎網。
2021,豆瓣怎么了?或者說,中文互聯網社區怎么了?
16 歲豆瓣的變與不變
2004 年 10 月,北京豆瓣胡同附近的星巴克多了一位 30 多歲的中年人。
每天下午,這名前清華大學的物理高材生、加州大學的博士,都會點一杯咖啡,然后打開用了三年、漆已開裂的蘋果筆記本,吭哧吭哧寫程序。
幾個月后,名叫“豆瓣評論”的頁面上線,其最初的功能,是討論書和電影。
就這樣,豆瓣的互聯網奇幻漂流,開始了。這個人,就是創始人阿北(楊勃)。
至于為什么被叫阿北。他自己的解釋是:因為搞不清我自己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,所以第一個網名起了“阿北”(“阿X”多是南方的稱呼習慣)。
這種自得、佛系的氣質與難以琢磨的執拗邏輯,也貫穿了豆瓣的命運。
2011 年C輪融資之后,豆瓣迫于投資壓力開始尋求商業變現。 2012 年,阿北透露豆瓣已經接近盈利,他說:“今年有的月份盈利,有的月份虧錢。”
而直到 2015 年,豆瓣仍然是接近盈利的水平。
但其實,豆瓣一開始就享受到了一個社區可以想象的諸多榮耀。
比如其上線后僅僅 9 個月的時間,就在被商業網站視為生命線的Alexa一路躥升進前4000,并擁有大量忠實用戶。而且,不同于其他網站動輒燒錢百萬的拉新風格,豆瓣前期投資僅有 20 萬元。
阿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,在豆瓣網的每十次點擊便會促成一次購買行為,可見粘性之高。
其次,在早期從硅谷Copy to China模式盛行時,豆瓣作為為數不多的具有中國原創特性的產品,受到了國內產品人、創業者和媒體輿論的一致肯定。
按照阿北的說法,豆瓣的期望,就是幫助人們發現更豐富的生活。
這樣的初衷,讓豆瓣的核心用戶畫像,成為圍繞著讀書、思考和熱衷于發現事物深刻面的沉思者。這不僅奠定了豆瓣的核心基因,也讓豆瓣文化越來越契合“精神角落”的宣言。
也是這樣的氛圍,讓豆瓣的產品設計,無論是諸如豆瓣說的上線下線、豆郵的改名妥協還是各種有趣又怪異的嘗試,都沒有偏離核心版塊的功能架構。
圖片
書影音,始終是豆瓣的內容源頭,它們分別對接豆瓣站內評分、排行榜、片單等主題,并逐步增加了電視、小說、同城等分區。
首頁的“動態/推薦、小組、集市和我的”四個版塊,則是在社區生態自發演變,與產品適應用戶群體及市場形勢的變革過程中,不斷調整的結果。
對于阿北的豆瓣而言,不變的還有“永遠不激進的商業化步伐,永遠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策略。”
成立四年后的 2009 年,豆瓣才有了自己的品牌廣告。時至今日,品牌廣告依然是豆瓣最大的營收來源。
2012 年 5 月 17 日,豆瓣電影開啟線上購票和選座位功能,但并沒有像貓眼那樣徹底成為一個為著電影市場服務的商業化地帶。
2017 年 3 月 7 日,豆瓣推出付費內容產品“豆瓣時間”,上線 5 天銷售額破百萬。但也關閉了一拍一、豆瓣東西、同城票務交易和一刻等長期沒有起色的業務。
2018 年,豆瓣開發了市集,開始售賣書籍和周邊,才算真正進入電商化潮流。
在社區“關于豆瓣”的頁面上,有一句話 16 年都沒有變過。
“豆瓣隨著這一個愿望產生。豆瓣不針對任何特定的人群,力圖包納百味。無論高矮胖瘦,白雪巴人,豆瓣幫助你通過你喜愛的東西找到志同道合者,然后通過他們找到更多的好東西。”
但另一方面,豆瓣自身的口碑正經歷顛覆性轉折,其社區地位也逐漸讓位于新一代的社交及內容社區。
2012 年就實現月活過億的豆瓣,在聲勢與商業化增長上,已經難以與今年剛剛月活過億的知乎相比,更不用說B站、小紅書等新興社區,以及抖音、快手、微博這樣的國民娛樂場地。
就連豆瓣深以為傲的影評的專業權威和公信力,也遭受了從媒體到用戶輿論的廣泛質疑。
更重要的是,十幾年的時間里,豆瓣的產品改動很多,大部分都是在與用戶的拉扯和博弈中進行,效果卻總是不溫不火。
它的變化,不像是知乎一樣瞄準了商業化增量而毅然向前,也不是像貼吧一樣有一個萬年不變的產品架構。
阿北說,一個最核心的理念,是豆瓣網希望以個人用戶為中心。所以多年來,豆瓣一直在野蠻的商業拓展與優雅地創造價值之間,尋找走鋼絲的平衡點。
但文青老用戶,并沒有因為感受到被體諒而消解不滿;各類小組用戶群,也不會因為體諒阿北而放棄自身的社區表達立場。
結果是, 16 歲的豆瓣不再是芳華正茂。并在 2021 年的互聯網高空,趔趄了一下。
Web2. 0 驕子,終將如云漂泊
2004 年,在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的第三年,出版社經營者O'Reilly和Media Live International舉辦了一場頭腦風暴論壇。
互聯網先驅兼O'Reilly副總裁Dale Dougherty指出,互聯網遠未"崩潰",而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,令人興奮的新應用程序和網站以驚人的規律性出現。
在會議之后的一年半時間里,“Web 2.0”一詞逐步深入人心,并爆發式增長到4. 7 億以上的相關鏈接。
圖片
在豆瓣誕生的同年,也是Web2. 0 概念引入中國的一年。
雖然阿北多次強調,他最初只是憑借著興趣吸引的理念,來創建豆瓣,而非追隨Web2. 0 的腳步。
但這并不妨礙,當時的人們曾將豆瓣視為Web2. 0 皇冠上的明珠,互聯網的驕子。
遺憾的是,明珠未能點燃閃電,而是長久地如云漂泊。
相比于以門戶和搜索網站為典型的Web1. 0 時代的退卻,用戶創造內容為主的交互和信息傳播方式,開始成為Web2. 0 的核心特征。
微內容,是Web2. 0 的一個關鍵詞。比如一則想法、一個評論、一張自拍、收藏的書簽、喜好的音樂列表、想結交的朋友等等。這些微內容,充斥在人們生活、工作、學習和精神流動的方方面面。
Web2.0,正是要負責這些內容的發現、傳播和消費—交易機制的建立。
豆瓣早期的書影內容,都屬于微內容的生產來源,且是優質的生產原料。但問題在于,這種生產機制,嚴重依賴于外部原創的書、影音等非用戶可決定的內容源。
如果社區生產的源頭,總是在外部或者同質化領域,那么這個社區的內容生態繁榮程度,其天花板肯定是顯而易見的,其內容競爭力也是難以不斷擴張的。
畢竟,從流量交易的角度去看,扶持類似于淘寶小B的大V創作者和MCN機構,以長久地提供標準化內容產品,是不可或缺的。
像B站一開始,也是借助番劇搬運、購買來吸引用戶。后來則變成了以UP主二創和原創內容為主的自生產基地,才能夠不斷擴充內容生產形式和體量,從而實現了B站平臺地位的破圈和躍升。
但豆瓣一直以來的文化,就是拒絕“粉絲”,甚至好友也被稱之為“友鄰”,以徹底貫徹以個體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策略。
其次,基于優質原料的深刻化生產,需要極大的生產成本支撐。
玩梗的膚淺或者單純的有趣,往往意味著如同空氣和水一般易得且大眾化。
比如抖音、快手的短視頻內容,不僅幾乎完全是依賴于用戶原創性內容生產和再生產的,視頻拍攝的消費門檻也在不斷降低,這讓平臺成為了真正的國民性內容消費場所。
況且,深刻的內核很容易重復且有排斥性,一旦一種深刻被受眾接受,其他方向的深刻化表達就顯得格格不入。所以,很多豆瓣的早期外來用戶,往往難以融入社區主流,且認為其固有文青用戶的內容特性,略顯矯情。
這也是深刻化生產動力不足,導致了評論區關于喝咖啡、談心情的文學性密度,遠大于專業性評判和信息給予的公共性的結果。
當然,更重要的是,任何具有理想主義的產品創始者,都會有一種天然的上帝心態,或者說是創造者意愿。
阿北說:“我們一直是,或者我一直是非常一廂情愿的、自作多情的,把用戶所有的稱贊和罵的聲音,都認為是我們的關愛。”
這種精神自洽性,也讓阿北對于對豆瓣的方向調整,具有更自信的獨斷意識。
在商業化上,阿北陶醉于抽象而具有公共美感的商業價值的達成,而非具象的、赤裸裸的商業交易的規模化實現。
他說:“豆瓣網的盈利模式很清楚,我們在用戶這端產生價值,用戶在購買東西時,我們在賣東西方得到我們的一些回報,是分成的方式。”
只要用戶在豆瓣上看到了書影音的推薦或者廣告,自行去購買,那么這種價值就算是達成了。豆瓣長期的商業目標,就是廣告分成而非把控渠道。
最終,在豆瓣的下廚房小組,變為下廚房APP的現實成功中。豆瓣并沒有想要成為另一個貓眼,也沒有造出另一個網易云音樂。
小而美的堅持,沒有烏托邦的彼岸
在產品理念上,阿北算得上是Web2. 0 核心價值觀的信徒,即小而美與不運營。
他曾自豪的宣稱:“我們從來不在社區里面,做話題或者是炒作的事情。所以我們其實沒有編輯,到現在一個都沒有。”
這種不運營策略,會讓用戶的體驗更加無拘束、無目的性,而感到舒服自在。
但同時,在移動互聯網時代,不運營的社區往往難以與全網事件形成及時聯動,或者形成穩定的以平臺為中心的社區文化管控慣性。
結果就是,豆瓣一方面逐漸成為被互聯網人遺忘的角落,另一方面難以高效完成與用戶的內部溝通,比如產品改版的不斷博弈內耗、小組崛起的自發生態帶來的沖擊,以及對時不時席卷而至的水軍缺乏防御。
畢竟,孱弱的商業能力會讓社區對于灰產的防御敏感度逐漸消解。像淘寶這類交易平臺,其風控關系到千千萬萬商家的真金白銀,而豆瓣這樣的情懷平臺,水軍更多是影響到用戶的觀感。
這并非說,豆瓣不重視用戶的體驗。而是體驗補償的多元化和用戶自身的消化彈性,使得平臺對于水軍防御的技術急迫性、現實剛性和經驗能力,都難以與灰產進攻處于同一層次。
就像俠客文化中,練太極養生的讀書人,自然不如鏢局里的高手們那樣能打。養生是生,護鏢是命,兩者之間的輕重緩急實不相同。
與此同時,小而美的執著,讓本有機會成為互聯網先驅的豆瓣,始終保持著小而美。
2012 年,是互聯網從PC全面轉向移動的一年。阿北也十分興奮:“幸好移動互聯網來了,這下問題簡單了,每個產品做一個獨立的APP就好了。”
顯然,一個商人會看到占據先機的龐然大物式的超級APP的誕生,一個信徒看到的則是多元化的烏托邦未來。
于是,豆瓣相繼推出豆瓣FM、豆瓣閱讀、豆瓣筆記、豆瓣電影、豆瓣小組、豆瓣同城、線上活動等 10 多款App。
圖片
前一段,處于臺風中心的是豆瓣。
12 月 1 日,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人約談豆瓣網主要負責人、總編輯。
對此,豆瓣發布公告稱從 2021 年 12 月 2 日 0 時- 2021 年 12 月 17 日 0 時期間,暫停“小組”回復功能的使用,并暫停小組“精選”頻道的內容更新。
更多的“敲打”,接踵而來。
12 月 9 日,豆瓣App因違規收集用戶信息,被工信部下架; 12 月 13 日,央視點名豆瓣存在水軍刷分控評現象。
圖片
全網的注意力、自媒體的輿論,已經很久沒有這樣聚焦在豆瓣之上了。只是這一次,不再是像數十年前的追捧與高歌,而是充滿了疑惑和質問。
但豆瓣,并非唯一受到監管注意的對象。
小紅書啟動新一輪“虛假營銷”專項治理,首批 29 個涉嫌虛假營銷的品牌被封禁; 2021 年 1 月至 11 月,新浪微博被實施 44 次處置處罰,共累計罰款 1430 萬元; 12 月 20 日,北京網信辦依法約談處罰知乎網。
2021,豆瓣怎么了?或者說,中文互聯網社區怎么了?
16 歲豆瓣的變與不變
2004 年 10 月,北京豆瓣胡同附近的星巴克多了一位 30 多歲的中年人。
每天下午,這名前清華大學的物理高材生、加州大學的博士,都會點一杯咖啡,然后打開用了三年、漆已開裂的蘋果筆記本,吭哧吭哧寫程序。
幾個月后,名叫“豆瓣評論”的頁面上線,其最初的功能,是討論書和電影。
就這樣,豆瓣的互聯網奇幻漂流,開始了。這個人,就是創始人阿北(楊勃)。
至于為什么被叫阿北。他自己的解釋是:因為搞不清我自己是南方人還是北方人,所以第一個網名起了“阿北”(“阿X”多是南方的稱呼習慣)。
這種自得、佛系的氣質與難以琢磨的執拗邏輯,也貫穿了豆瓣的命運。
2011 年C輪融資之后,豆瓣迫于投資壓力開始尋求商業變現。 2012 年,阿北透露豆瓣已經接近盈利,他說:“今年有的月份盈利,有的月份虧錢。”
而直到 2015 年,豆瓣仍然是接近盈利的水平。
但其實,豆瓣一開始就享受到了一個社區可以想象的諸多榮耀。
比如其上線后僅僅 9 個月的時間,就在被商業網站視為生命線的Alexa一路躥升進前4000,并擁有大量忠實用戶。而且,不同于其他網站動輒燒錢百萬的拉新風格,豆瓣前期投資僅有 20 萬元。
阿北在接受采訪時表示,在豆瓣網的每十次點擊便會促成一次購買行為,可見粘性之高。
其次,在早期從硅谷Copy to China模式盛行時,豆瓣作為為數不多的具有中國原創特性的產品,受到了國內產品人、創業者和媒體輿論的一致肯定。
按照阿北的說法,豆瓣的期望,就是幫助人們發現更豐富的生活。
這樣的初衷,讓豆瓣的核心用戶畫像,成為圍繞著讀書、思考和熱衷于發現事物深刻面的沉思者。這不僅奠定了豆瓣的核心基因,也讓豆瓣文化越來越契合“精神角落”的宣言。
也是這樣的氛圍,讓豆瓣的產品設計,無論是諸如豆瓣說的上線下線、豆郵的改名妥協還是各種有趣又怪異的嘗試,都沒有偏離核心版塊的功能架構。
圖片
書影音,始終是豆瓣的內容源頭,它們分別對接豆瓣站內評分、排行榜、片單等主題,并逐步增加了電視、小說、同城等分區。
首頁的“動態/推薦、小組、集市和我的”四個版塊,則是在社區生態自發演變,與產品適應用戶群體及市場形勢的變革過程中,不斷調整的結果。
對于阿北的豆瓣而言,不變的還有“永遠不激進的商業化步伐,永遠以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策略。”
成立四年后的 2009 年,豆瓣才有了自己的品牌廣告。時至今日,品牌廣告依然是豆瓣最大的營收來源。
2012 年 5 月 17 日,豆瓣電影開啟線上購票和選座位功能,但并沒有像貓眼那樣徹底成為一個為著電影市場服務的商業化地帶。
2017 年 3 月 7 日,豆瓣推出付費內容產品“豆瓣時間”,上線 5 天銷售額破百萬。但也關閉了一拍一、豆瓣東西、同城票務交易和一刻等長期沒有起色的業務。
2018 年,豆瓣開發了市集,開始售賣書籍和周邊,才算真正進入電商化潮流。
在社區“關于豆瓣”的頁面上,有一句話 16 年都沒有變過。
“豆瓣隨著這一個愿望產生。豆瓣不針對任何特定的人群,力圖包納百味。無論高矮胖瘦,白雪巴人,豆瓣幫助你通過你喜愛的東西找到志同道合者,然后通過他們找到更多的好東西。”
但另一方面,豆瓣自身的口碑正經歷顛覆性轉折,其社區地位也逐漸讓位于新一代的社交及內容社區。
2012 年就實現月活過億的豆瓣,在聲勢與商業化增長上,已經難以與今年剛剛月活過億的知乎相比,更不用說B站、小紅書等新興社區,以及抖音、快手、微博這樣的國民娛樂場地。
就連豆瓣深以為傲的影評的專業權威和公信力,也遭受了從媒體到用戶輿論的廣泛質疑。
更重要的是,十幾年的時間里,豆瓣的產品改動很多,大部分都是在與用戶的拉扯和博弈中進行,效果卻總是不溫不火。
它的變化,不像是知乎一樣瞄準了商業化增量而毅然向前,也不是像貼吧一樣有一個萬年不變的產品架構。
阿北說,一個最核心的理念,是豆瓣網希望以個人用戶為中心。所以多年來,豆瓣一直在野蠻的商業拓展與優雅地創造價值之間,尋找走鋼絲的平衡點。
但文青老用戶,并沒有因為感受到被體諒而消解不滿;各類小組用戶群,也不會因為體諒阿北而放棄自身的社區表達立場。
結果是, 16 歲的豆瓣不再是芳華正茂。并在 2021 年的互聯網高空,趔趄了一下。
Web2. 0 驕子,終將如云漂泊
2004 年,在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滅之后的第三年,出版社經營者O'Reilly和Media Live International舉辦了一場頭腦風暴論壇。
互聯網先驅兼O'Reilly副總裁Dale Dougherty指出,互聯網遠未"崩潰",而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,令人興奮的新應用程序和網站以驚人的規律性出現。
在會議之后的一年半時間里,“Web 2.0”一詞逐步深入人心,并爆發式增長到4. 7 億以上的相關鏈接。
圖片
在豆瓣誕生的同年,也是Web2. 0 概念引入中國的一年。
雖然阿北多次強調,他最初只是憑借著興趣吸引的理念,來創建豆瓣,而非追隨Web2. 0 的腳步。
但這并不妨礙,當時的人們曾將豆瓣視為Web2. 0 皇冠上的明珠,互聯網的驕子。
遺憾的是,明珠未能點燃閃電,而是長久地如云漂泊。
相比于以門戶和搜索網站為典型的Web1. 0 時代的退卻,用戶創造內容為主的交互和信息傳播方式,開始成為Web2. 0 的核心特征。
微內容,是Web2. 0 的一個關鍵詞。比如一則想法、一個評論、一張自拍、收藏的書簽、喜好的音樂列表、想結交的朋友等等。這些微內容,充斥在人們生活、工作、學習和精神流動的方方面面。
Web2.0,正是要負責這些內容的發現、傳播和消費—交易機制的建立。
豆瓣早期的書影內容,都屬于微內容的生產來源,且是優質的生產原料。但問題在于,這種生產機制,嚴重依賴于外部原創的書、影音等非用戶可決定的內容源。
如果社區生產的源頭,總是在外部或者同質化領域,那么這個社區的內容生態繁榮程度,其天花板肯定是顯而易見的,其內容競爭力也是難以不斷擴張的。
畢竟,從流量交易的角度去看,扶持類似于淘寶小B的大V創作者和MCN機構,以長久地提供標準化內容產品,是不可或缺的。
像B站一開始,也是借助番劇搬運、購買來吸引用戶。后來則變成了以UP主二創和原創內容為主的自生產基地,才能夠不斷擴充內容生產形式和體量,從而實現了B站平臺地位的破圈和躍升。
但豆瓣一直以來的文化,就是拒絕“粉絲”,甚至好友也被稱之為“友鄰”,以徹底貫徹以個體用戶為中心的服務策略。
其次,基于優質原料的深刻化生產,需要極大的生產成本支撐。
玩梗的膚淺或者單純的有趣,往往意味著如同空氣和水一般易得且大眾化。
比如抖音、快手的短視頻內容,不僅幾乎完全是依賴于用戶原創性內容生產和再生產的,視頻拍攝的消費門檻也在不斷降低,這讓平臺成為了真正的國民性內容消費場所。
況且,深刻的內核很容易重復且有排斥性,一旦一種深刻被受眾接受,其他方向的深刻化表達就顯得格格不入。所以,很多豆瓣的早期外來用戶,往往難以融入社區主流,且認為其固有文青用戶的內容特性,略顯矯情。
這也是深刻化生產動力不足,導致了評論區關于喝咖啡、談心情的文學性密度,遠大于專業性評判和信息給予的公共性的結果。
當然,更重要的是,任何具有理想主義的產品創始者,都會有一種天然的上帝心態,或者說是創造者意愿。
阿北說:“我們一直是,或者我一直是非常一廂情愿的、自作多情的,把用戶所有的稱贊和罵的聲音,都認為是我們的關愛。”
這種精神自洽性,也讓阿北對于對豆瓣的方向調整,具有更自信的獨斷意識。
在商業化上,阿北陶醉于抽象而具有公共美感的商業價值的達成,而非具象的、赤裸裸的商業交易的規模化實現。
他說:“豆瓣網的盈利模式很清楚,我們在用戶這端產生價值,用戶在購買東西時,我們在賣東西方得到我們的一些回報,是分成的方式。”
只要用戶在豆瓣上看到了書影音的推薦或者廣告,自行去購買,那么這種價值就算是達成了。豆瓣長期的商業目標,就是廣告分成而非把控渠道。
最終,在豆瓣的下廚房小組,變為下廚房APP的現實成功中。豆瓣并沒有想要成為另一個貓眼,也沒有造出另一個網易云音樂。
小而美的堅持,沒有烏托邦的彼岸
在產品理念上,阿北算得上是Web2. 0 核心價值觀的信徒,即小而美與不運營。
他曾自豪的宣稱:“我們從來不在社區里面,做話題或者是炒作的事情。所以我們其實沒有編輯,到現在一個都沒有。”
這種不運營策略,會讓用戶的體驗更加無拘束、無目的性,而感到舒服自在。
但同時,在移動互聯網時代,不運營的社區往往難以與全網事件形成及時聯動,或者形成穩定的以平臺為中心的社區文化管控慣性。
結果就是,豆瓣一方面逐漸成為被互聯網人遺忘的角落,另一方面難以高效完成與用戶的內部溝通,比如產品改版的不斷博弈內耗、小組崛起的自發生態帶來的沖擊,以及對時不時席卷而至的水軍缺乏防御。
畢竟,孱弱的商業能力會讓社區對于灰產的防御敏感度逐漸消解。像淘寶這類交易平臺,其風控關系到千千萬萬商家的真金白銀,而豆瓣這樣的情懷平臺,水軍更多是影響到用戶的觀感。
這并非說,豆瓣不重視用戶的體驗。而是體驗補償的多元化和用戶自身的消化彈性,使得平臺對于水軍防御的技術急迫性、現實剛性和經驗能力,都難以與灰產進攻處于同一層次。
就像俠客文化中,練太極養生的讀書人,自然不如鏢局里的高手們那樣能打。養生是生,護鏢是命,兩者之間的輕重緩急實不相同。
與此同時,小而美的執著,讓本有機會成為互聯網先驅的豆瓣,始終保持著小而美。
2012 年,是互聯網從PC全面轉向移動的一年。阿北也十分興奮:“幸好移動互聯網來了,這下問題簡單了,每個產品做一個獨立的APP就好了。”
顯然,一個商人會看到占據先機的龐然大物式的超級APP的誕生,一個信徒看到的則是多元化的烏托邦未來。
于是,豆瓣相繼推出豆瓣FM、豆瓣閱讀、豆瓣筆記、豆瓣電影、豆瓣小組、豆瓣同城、線上活動等 10 多款App。
圖片